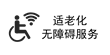每次只要到开远新地标——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转悠时,不自觉的要绕到南正街街区的西边也就是原武庙街地段驻足观望,总想找寻一些武庙街的痕迹,因为这里曾是我外婆家,溢满了我的童年乡愁。
乡愁是人类共同的情感,因为乡愁,我们的精神才有了归依,心灵才有了家园。它陪伴在我们的左右和我们一起成长但却不会老去,永远那么充满活力,无私的与我们相伴前行,不离不弃,无形却无处不在。武庙街留下了我无忧无虑且充满快乐的童年时光,对武庙街的回忆,就是对童年的追忆。
在我心中,武庙街是一条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巷。一步一景,每个角落都蕴藏着往事。
开远自元代建置设州后至晚清,城区房屋建设局限于旧城墙内,除私宅外,尚有衙署、州学、社仓、作坊、店铺等建筑。武庙街在明清时期叫西门街,民国时期因街上建有关圣庙(武庙)而得名,文革期间改为要武街,文革后又改回武庙街并沿用至今。但当年的武庙早已荡然无存。街上还有一座明清时期的衙署。另一座昭忠祠民国年间曾作他用,后作为水电局职工宿舍,也被拆迁。道路建筑为毛石板路面,中间铺3列长条石,两边镶块石。1952年后,随着开远城市建设的发展,旧城墙拆除,街道截直、拓宽、改筑、新建。武庙街北接灵泉西路,南接文化街头,西接文化街,分司巷并入武庙街。至1990年时,武庙街改为混凝土路面,全长377米,道宽5--6米。武庙街的房屋建筑种类多样,有土基房、木头房、砖混房、青石房等,基本都是私宅,且大多是平房。保留着民清时期街巷肌理的武庙街,虽然房屋建筑老旧,但沉淀着历史的芳华,显得既古典又年
武庙街可以称为开远地方校办幼儿园教育之始发地。开远市教委第一幼儿园前身是民国32年(1943年)3月在宁远镇中心学校(后名灵泉小学)内附设的幼稚部,实行半日制,中午幼儿入园,下午由老师送幼儿回家。民国35年迁至武庙(也就是武庙街南段)独立办学,称为正中保育园。1949年改称幼稚园。此期间有园长、教师1-3人,入园幼儿数十人。1950年后仍为走读制,时有幼儿3班103人,教职工5人。1952年更名为开远县幼儿园。次年,在园幼儿增至286人,有教职工9人。1958年又迁入武庙街北段(西邻灵泉小学),改称久安幼儿园,主要招收县直机关干部子女。为“解放妇女劳动力”、适应“大跃进”的需要,同时增办了婴儿班和小幼班,直到1960年再次迁回灵泉西路团结巷现址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都在武庙街办学。
武庙街还是东方红小学最初的办学旧址。1962年8月,城关公社利用原公共食堂和幼儿园的场地设施兴办的东方红小学,校址设在武庙街中段西侧,学校北侧与灵泉小学比邻。学校初为民办,由生产队选派民办教师11人。历史形成生源多为城区农民子女。1968年并入比邻的灵泉小学,1972年学校小学部分与附属初中部分离,但一直沿用东方红小学校名。直到1983年后,城关镇社员集资13万元,并优价出售土地,市教育局拨款37万元,在西山路新建校址并迁入办学,转为公办小学至今。
记得1975年我上学时,在东方红小学读了两年,因为父母均在解化上班,不仅忙工作,而且小我4岁的弟弟需要照顾,我就被送到离外婆家不到100米的东方红小学就读,直到三年级才转到解化子弟小学读书。当时明清时期遗留的衙署就是进学校的大门,低年级的教室就设在衙署里,我们每天上学都要跨上高高的衙署大门台阶进到教室。衙署是木质结构,冬暖夏凉,夏天进到教室都有阵阵寒意来袭。教室内光线偏暗,每天上课都期盼太阳光从窗户外倾泻进来,顿时觉得温暖如故,上课的心情都出奇地大好。学校课余时间还要求学生“积肥”支援农业发展,并规定每周四缴纳一撮箕肥料,计入学期考核。那时的猪、鸡、鹅、鸭、狗等动物都是放养,武庙街上随处可见各类动物奔跑觅食。我们每天放学后就手拿撮箕和小铲铲,跟在各种动物后面清扫粪便,速度慢的还抢不到。学生们甚至跑到南正街、北正街等其它街道去找“肥”,实在积不够的就想办法在“肥”里加入“灶窝灰”和碎稻草搅拌均匀,以增加重量,确保完成“积肥”任务,以至于武庙街及附近街道每天都被清扫的干干净净。
在我心中,武庙街是一条有温度的小巷。短短的距离,深深的眷恋,用自己的脚步和欣喜,丈量着回家的路。让记忆和故乡的光影,在这一刻重逢。
外婆家在武庙街14号。外婆和外公共育有7个子女,其中4个儿子、3个女儿,我妈排行老五。外公的祖上曾当过清朝的小吏,外公小时候上过私塾,算是家里有学问的人了,外公话语不多,但和蔼可亲,平易近人,很爱读书看报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。那时我父亲会定期找上一些已经过期的《参考消息》、《云南经济报》、《半月谈》等报刊,利用周末到外婆家聚餐的时间拿给外公看,那可是外公一周的精神食粮。每天只要一有时间,他都会戴上放大镜认真仔细的阅读,并经常给我们孙辈谈故论今,教我们做人立德的道理。
外婆虽然不识字,但待人热情,乐于助人,人缘极佳,谁家孩子没人领会送来外婆家和我们一起玩;谁家炒菜差点盐巴、葱、姜、蒜会来找外婆要;谁家发生矛盾也是找外婆评理调解。外婆是武庙街有名的杨二妈(因为外公排行老二),男女老少都这样称呼她,后期随着年龄增大后又被大家称为杨二奶。外婆脑子灵活,精明能干,会做生意,利用家里房子临街且1949年以前的武庙街一直是山区赶街的马帮及山民必经之地的优势,利用空余时间,带着二姨妈手工缝制一些衣品和鞋子,并代购代办各种山货和物品,逢街天打开家里的门板窗户(平时不全开)做生意,收入用来补贴家用,不然一大家人的开销大呢,这个家真不好当。
听外婆讲,我大舅小时候的尿布都是用清朝时期祖上遗留废除的“官服”前后搭片改做的。大舅自开远灵泉小学毕业后考入开远县立初级中学,后再考入开一中简易师范班,品学兼优,接受进步思想,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。1945年8月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,积极参加了“一二一”学生爱国运动,并秘密地加入了“民青”(共青团的前身),后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,边完成学业,边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相关任务和工作。至1949年12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十支队组建护乡第九团,以配合刘、邓大军解放云南和开远家乡,大舅担任护九团二中队一分队的政治服务员,随部队转战三迤大地,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英勇战斗。1950年1月,又任开远县公安局公安队指导员,在清匪反霸、镇压反革命分子等运动中,忠实地履行了人民卫士的神圣使命。1954年经党组织选送,大舅进入重庆市公安学校(重庆警察学院的前身)深造学习。毕业后被分配至云南省公安厅工作,但大舅多次向党组织请求,到急需公安骨干的边疆艰苦地区工作,后再分配至红河州公安局政保科任侦讯股长。为维护国家安全,打击反革命敌对势力,深入红河州各县指导和参与重大案件的侦破。1959年2月,元阳县第四区(蛮邦)土匪暴动,烧杀无辜,无恶不作,大舅刚从云锡公司侦破一起反革命案件返回局里,即主动请战,顾不上休息,连夜奔赴元阳蛮邦战场,配合解放军部队对土匪进行围剿,在战斗中英勇牺牲,享年31岁,践行了投笔从戎、为国捐躯的人生志向。1959年3月,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,并收录入红河州英烈大典中。
受大舅的影响,我二姨妈、三姨妈找对象都是以大舅为参照。二姨爹是1948年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离休干部;三姨爹也是1948年从河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并随部队南下的离休干部。我母亲虽然没有找革命军人,但我父亲是昆明工业学校(昆明工学院的前身)毕业分配到解化厂并担任解化生产副厂长十年之久的企业干部。
我四舅小时候脾气大,吃饭爱用剩菜碗里的油来拌饭,说油呵呵呢吃着香,每天吃饭宁可等着大家吃完后再并剩菜碗底拌饭。四舅读书刻苦用功,在开一中时下午放学不回家继续在校自学,直至晚自习后才回,晚饭、宵夜合并一起吃。有一次做错事被外婆斥责后赌气离家出走,二估二估呢,外婆悄悄地跟随其后,看他究竟要去哪里?只见四舅饿着肚子在大街小巷漫无边际地游荡,最后还是外婆主动拉着他回家吃饭。四舅高中毕业考上了云南工学院,成为七姊妹中唯一的大学生。
外婆家的老房子在解放时曾经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“护九团”的一个小分队驻扎过几天。1950年1月18日“边纵”十支队护九团和“边纵”二支队十四团解放了开远县城。时值人民解放军第13军占领蒙自机场解放蒙自县城后,于1950年1月25日第13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回撤开远,并举行入城仪式。在这之前的近一个星期内,是“边纵”部队在维护地方治安和清剿残敌。“边纵”部队是分散于城内各个点驻扎的。外婆家老房子厨房旁边有一个大院子,包括那幢青砖楼房及很多民房均是1949年后才盖的,之前是外婆家的后菜园地。虽然县城解放了,但“边纵”部队仍是风餐露宿,生活艰苦,供给困难,“边纵”的这个小队(“边纵”部队着青蓝色军装佩红领章、头戴八角布帽有红五星)先是驻扎后院菜园地内,就地支锅煮饭、火烧辣子沾盐巴就着一锅汤菜下饭。让外婆老心疼啦,带上我二姨妈(那时二姨妈初中毕业后在家闲居,在待嫁期间一直协助外婆领弟妹、做家务等,那时七舅尚未断奶,我妈也就八、九岁读小学)一到吃饭时即从家中用大汤碗舀了几大碗酸菜等酱菜送给“边纵”这个小队佐餐下饭。一开始这个“边纵”小队纪律严明,不肯收下,老外婆解释说“我大儿子也是“边纵”的,跟你们穿一样的衣裳,他叫杨映昆。不怕得,你们放心地吃,有咸菜才好下饭,我们都是一家人……。”(解放开远县城后,大舅曾经抽空回过一次家,向家中报个平安后即又归队了)。外婆这样一说,这个“边纵”小队的战士就亲切起来,左一声大妈、右一声大妈地叫,才肯收下每餐送去的酸菜等下饭咸菜。外婆就邀请“边纵”小队到家中楼上居住,说房子宽呢,菜园子晚上风大又冷…。但纪律严明的这个“边纵”小分队说不打扰群众,硬是住在菜园子里直到撤走。
在我心中,武庙街是一条快乐的小巷。这里有外公的气息,有外婆的味道,那是童年最需要依靠的力量。
外婆家的老房子是一栋二层楼的临街传统木板房。面积有200多平方米,房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八十年代初,外婆家在房子四周砌了一堵红砖墙,以保护年代久远的木板房。房屋以木构架为支撑,全部由粗木材建造,每个接口都是用榫子相互拉扣,非常坚固结实。屋顶则是用青瓦铺出翘脚檐枋。房屋不仅冬暖夏凉、抗潮保湿、透气性强,还蕴涵着醇厚的街巷气息,淳朴典雅。雨季当湿度大时木屋能自动吸潮,干燥时又会自动释放水分,起到天然调节的作用。据说木板房抗震系数高,但不知真假。只记得1976年夏天开远发生过一次较大地震,当时电灯四处摇晃,明显感觉房子都在抖动,大家吓得纷纷跑到街上空旷处躲避,晚上也不敢回家,在外打地铺睡觉,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个把星期。只有外婆家感觉震感不明显,全家人都没有搬到外面睡觉。很多邻居小伙伴跑来跟我要求,说街道外面蚊虫叮咬,晚上要来我家睡。善良的外婆都一一答应,让他们在一楼客厅打地铺排成一排的睡,殊不知5、6个小孩聚在一起却很兴奋,一晚上聊天、打闹到深夜都不睡觉,直到外公出来制止才乖乖睡去,那几天外婆家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。
在外婆家,我每天起床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趴在外婆家二楼的木窗户上,静静地看着房檐排水瓦片上自然生长的一小撮红色太阳花迎风绽放。我每天最喜欢喝的水是外婆家后院旁大青石水井里的甘甜井水。我每天最喜欢走的路是打着赤脚在武庙街的毛石板路上跑来跑去。特别是雨中漫步武庙街,古色古香的毛石板路曲径悠长(八十年代改为混凝土路),与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遥相重叠,意境深远。
外婆家中的大卧室左右两边放置大、小床各一张,两床之间靠花窗处摆放一张抽屉桌,这张桌子是外公、外婆结婚时所添置。卧室的房顶正中央用铁钉打了一个挂钩,挂钩上长年累月挂着一个竹篮,这个竹篮可是外婆的宝贝,因为里面经常会放着猫屎糖、沙糕、荞饼、水果糖等好吃的食物。由于家里孩子多,每次外婆都是计算着时间拿出来定量分给子女和孙辈们吃。外婆以为食物挂在房顶我们小孩够不着吃,殊不知我们几个表姊妹悄悄商量,趁外婆不在的时候,搬颗高凳子垫着,伸手就拿到食物,然后躲起来分享。几个表姊妹不敢把竹篮里的东西吃完,每次偷吃一点。刚开始外婆发现东西少了一直没太在意,是有一件事让外婆彻底发现了我们干的坏事。外婆有位干女儿是蒙自新安所的,新安所的石榴也是全省有名的。每年石榴成熟时,干女儿都会给外婆送些自家种的石榴,外婆还是一如既往地放进卧室的竹篮里,我们也估着时间偷吃竹篮里的石榴。直到有一天我们正在搬凳子拿石榴时,恰好被外婆逮了个正着,外婆连连说没想到我们偷吃还真有一套,真是人小鬼大。
在我上小学前,有一件帮倒忙的事情让我记忆犹新。外婆家隔壁的李阿姨一家很勤劳,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根据季节种植不同的蔬菜,除街天用扁担挑到菜市场卖外,平时也会用箩筐装着放在家门口售卖。李阿姨家的小女儿小芬年龄和我相仿,我经常会去找她玩。有一天早上李阿姨家收割了些菠菜,因为忙其它事,就让女儿小芬到门口帮忙看摊点,加之菠菜绑得很大很结实,告知她每把卖1角钱。那天早上我吃完早点转悠到她家门口时,恰好看见小芬摊位上买菜的路人很多,我就走上去帮她一起卖。买菜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,一开始买菜的人可能也觉得菠菜的价格实惠,没有讲价,直接买了就走。后来聚集的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:小妹妹,菜太贵了,给你1角5分买两把如何?小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,把目光投向我,我当时感觉听着1角5分买2把很舒服,也没帮她算算这样的话两把就亏了5分钱,要知道5分钱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可以买很多东西了。我一个劲地跟她点头说:可以卖呢!结果当她同意卖时,一大筐菠菜没多大功夫就被一抢而空。我还暗自高兴帮她收了个早工,跟在她后面准备去她家玩。谁知才进家门,她妈问她卖菜的情况,她讲了之后她妈说话的声调立马提高了八度,劈头盖脸一阵痛骂,大骂她不会算账把菜卖亏了。我一看势头不对,立马掉头跑了出来,害怕连我也跟着一起挨骂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去她家找她玩,主要也是因为内疚让她把菜卖便宜了,这件事也让我深怀歉意至今。
武庙街也是我生命的第二次重生之地。小时候在外婆家时,在街上玩耍基本没有大人看护。我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,爸爸妈妈他们休息领着弟弟也到外婆家集合了。下午5点多,一大家子人都在厨房忙着做饭、谈天说地,我自己跑到外婆家斜对面的街上玩耍,那时外婆家街对面有一条排污沟贯通整条武庙街,沟里集满了污泥,上面没有盖板。我一个人在宽约50、60公分、深约40、50公分的沟边跳来跳去,结果发现鞋带松了,当我低下头去系鞋带时,因低头的冲力太大竟一头栽进排污沟里。只记得我的身体很快就往下沉到污泥里,口、鼻里塞满了污泥,只有两只脚漏在外面使劲蹬,当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时,忽然被人倒提着两只脚拉出了排污沟,只看见是一位叔叔把我提出来放到了路边,他手上和身上也沾了很多污泥,他只是用手拍了拍污泥就走了,而我只知道张着嘴大哭着往外婆家里走。家里人听到外面小孩的啼哭声后,我爸爸拉着弟弟出来看,居然没认出全身沾满污泥的我,还以为是别家的孩子,又转身回去了,我哭着跟在他俩后面进到外婆家。妈妈看到后向我问清情况,赶忙到街上寻找那位救我的叔叔,但那人已走了。而我被妈妈直接拉到院子里的大青石水井旁,用桶提水上来洗了半个小时才洗干净全身的污泥。后来妈妈经常跟我说,是那位好心的叔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,有朝一日找到他一定要当面致谢,可至今也没有找到那位好心的叔叔。
在我心中,武庙街是一条幸福的小巷。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巷,我的小巷没有浓墨重彩,没有喧嚣浮华,它宁静深远,厚重不凡,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,也承载了我未来所有的期许。
武庙街的烟火气息很浓,日子是平淡而充实的,不论是老有所乐的翁妪、天真活泼的孩童还是时髦亮丽的青年,每个人都在平淡中演绎着不同的人生。街上居住的人员除部分老开远人外,还有许多外来人口,当兵、当工人、当老师的、在政府机关工作的、种地的、做生意的,可谓工农兵学商样样俱全。街上最有名的店铺数老钟家的面条加工厂、梁记鸡肉米线店、阿菊烧烤店以及李建华家的服装缝纫店。
街上的很多家庭多才多艺,吹拉弹唱各有所长。我六舅就擅长拉二胡,我妈妈擅长吹口琴,我六舅妈则喜欢唱歌、跳舞,隔壁张大叔的小号吹得“贼溜”,王阿姨还会唱京剧,刘大爹则负责指挥。每到周末闲暇时,吃过晚饭的邻居们拿着自己的乐器,抬着小板凳一起集中在外婆家房子后面的院子里自娱自乐,排练下乐曲,唱唱山歌,偶尔也会唱唱《红灯记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等样板戏选段。那也是小孩最喜欢参与的活动,我们总是早早就去凑热闹,跟着大人们手舞足蹈,释放天性。记得住在武庙街头老八婆家的小女儿王丽媛是开远县文艺宣传队(市歌舞团的前身)的舞蹈演员,我从小就叫她小孃嬢,她很喜欢我,经常带我出去玩。那时宣传队正在排练舞剧《沂蒙颂》,小孃嬢担任该剧的女主角,她每周二、四晚上排练时,就来外婆家带我去看她练功。在宣传队排练室,看着小孃孃换上舞蹈鞋,对着大镜子、踮起脚尖在长长的把杆上练功真是一种美的享受。特别是看着她和男主角在音乐的伴奏下合跳时,舞姿优美典雅,看的我如痴如醉。我从小喜欢唱歌、跳舞也是那个时候受大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那时候不论是学校还是幼儿园都没有课外声乐、舞蹈培训班,整条街喜欢跳舞的小孩会自发聚集到武庙街头的粮店旁练功,压腿、劈叉、撕“一字马”、打“倒踢”等等,看谁做的最到位,还有跳得好的小姐姐纠正动作,大家都是自学成才,乐在其中。虽然我妈妈没有教过我乐器,但我工作后报名参加了单位的业余管乐队学习了两年的黑管。这些爱好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,也让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,并且受用一生。
时光荏苒,岁月变迁。我小学三年级转到解化子弟学校读书后,外婆仍然每个周末都要召集住在开远的儿女回家小聚。我们也很喜欢到外婆家,一来可以听她讲武庙街的趣闻轶事,二来可品尝她做的美味饭菜。我女儿出生后更是经常被外婆念叨带去看她,直到2003 年外婆93岁高龄去世(外公70多岁就去世了)。外婆家的老房子也被舅舅们出租几年后又转卖出去。自此,我也很少再到武庙街了。
2017年至2021年,作为开远市南园片区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带动城市更新的试点项目——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开始动工建设,武庙街也被纳入拆迁范围。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精雕细琢,建成13幢具有民国风格的低层商业建筑和530米的步行街,配套建设了文化馆、九天阁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,占地面积78.79亩,房屋总建筑面积43163.19平方米,最大限度“修旧如旧、建新如故”的南正街迎来迭新重启。武庙街这条有温度、有厚度的小巷消失了,因为它被拆得片甲不留。但武庙街带给我的记忆是永恒的,这里有一段丁香般淡淡的乡愁,血脉永远在这里流淌。在我心中,武庙街并没有消失,因为它融入了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而重获新生,并将承袭着开远商贸文化的老街记忆开启新的征程。(来源:开远文旅公众号 文:开远市政协 任涛)
 滇公网安备53250202000205号网站标识码:5325020004
滇公网安备53250202000205号网站标识码:5325020004 x
x
 无障碍浏览
无障碍浏览 长者模式
长者模式




 首页
首页

 开远概况
开远概况

 政务资讯
政务资讯

 政府信息公开
政府信息公开

 政务服务
政务服务

 政民互动
政民互动

 投资开远
投资开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