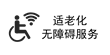你知道吗?开远城中有一条“分司巷”,这条普普通通的小巷,却藏着一段影响深远的土流博弈史,诠释着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漫长角力。
《开远市志》记载:正统元年(1436年),首次任命汉官张安为阿迷州知州。成化十二年(1476),普氏土官被废黜,为阿迷州第一次改土归流。
要知道,开远虽然早在汉朝就被纳入了华夏版图,但真正彻底从文化上融入却是明朝。明朝吸取了元朝的教训,通过军事、行政、经济、文化四个维度的系统性变革,强化了对阿迷州等边疆的统治,促进了边疆开发与民族融合,使阿迷从边地屏障逐渐转化为中国的有机部分。

开远,这座边城历经数百年风雨,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深化与多元文化的交融。
军事建构,卫所屯戍与军事威慑
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沐英率军平定云南后,朱元璋诏命:“以云南既平,留江西、浙江、湖广、河南四都司兵守之,辖制要害”,并行军屯,在临安卫下辖设阿迷守御千户所。这支由汉族将士组成的军事力量,不仅承担着防御安南、弹压土司的职责,更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向西南渗透的先锋队。明朝推行军屯、民屯和商屯,大量汉族移民迁入阿迷州,开垦荒地,推广中原农耕技术。军屯以卫所士兵为主(如临安卫),民屯则由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参与,形成“三分守城,七分屯种”的军民结合体系。所以,凡是如今叫营、所、堡、铺、哨的,诸如大庄、驻马哨、三台铺等等,都是明代军屯的遗留;而从李家村、十里村、毛家寨等地名,则可溯源明代移民屯田。军屯制度的推行使得江南稻作技术在此落地生根,大庄、驻马哨等带有鲜明军事色彩的地名,见证着"三分守城,七分屯种"的屯垦体系如何重塑边疆的土地肌理。此外,明廷通过军事打击逐步削弱土司武装,在阿迷州周边修筑关隘(如禄丰关、盘江关),控扼交通要道,防止土司割据与外敌侵扰。

行政重构,土流博弈的世纪棋局
明洪武十五年(1382),复置阿迷州,隶属于临安府管辖。土司制度元朝开始实行,明后期开始废除土司制度,改用流官制,即“改土归流”,1476年普氏土官的革除,标志着首次改土归流的尝试。尽管这一进程充满反复——直至雍正三年(1725年)最后一任土司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但流官体系的建立已然不可逆转。
土流博弈的战场,居然是城池。正统元年(1436年),首任流官张安在灵泉村另筑新城,开创了"一城两治"的奇特景观:东山南麓的流官衙门悬挂着"拱极门"匾额,东山那边的土司宅邸仍飘扬着彝族图腾旗帜。
阿迷州虽是元朝设立,但元朝时期开远还没有大规模的城池,当时滇南地区仅临安府建有城池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重修州城,筑土城并设四门。明正统元年(1436年),首任流官张安((四川眉州人)赴任阿迷州知州,次年新建知州府于灵泉一带(位于落蒙村,落蒙河曲折绕于州府前),城高丈余,设东(迎旭)、南(朝宗)、西(望广)、北(拱极)四门。相当于此时有了两个阿迷城,这也是土司制度顽固性的体现。开远原由土知州管治,直到明代正统年间,朝廷才派遣流官参与管理。张安到阿迷州上任后,土司表面上对他有求必应,背地里却事事使绊子。这让张安感到十分不安,思来想去,就到开远坝另筑一座新的阿迷城,另盖一座新的流官衙门,隔东山与土司划山而治。于是,就有了如今的开远城。普氏土司偏安于傍甸乡,隔着东山和大黑山天然之界,土流并存,一州两制,封建地主经济与封建领主经济长期并存。后来,分司就分到了城里。开远城中还留着一个“分司巷”,上连武庙街,下连南正街,据说就是东山土司李阿侧康熙五年(1665)重授土知州后,就以这条巷与流官划界而治。所以民间谚语说:“斗大阿迷城,一城两州官,巷南流官治,巷北土司守”。明清两朝,开远城逐渐成型。初期阿迷城墙都是泥土夯筑,到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开远城“易以砖,周三里”,改成了石墙。城池多次经历战乱,大西军李定国攻陷后毁坏,到了清朝康熙九年,1670年再次重建石墙。当时阿迷城并不大,民谚“省城九里九,府城六里六,州城三里三”,城中“六街九巷”,清一色的灰瓦,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。

经济开发:农耕文明带来产业勃兴
明代阿迷州的经济发展堪称边疆开发的典范。
洪武末期,移滇汉民赵升倾全家之力以30年时间,疏浚河道、开凿水渠,建成了环开远坝区的东沟和西沟,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。水稻、玉米、小麦等粮食作物广泛种植,经济作物如甘蔗、茶叶也逐渐发展,尤其是河谷地带成为重要产粮区。阿迷州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丰富,明代对银、铜、锡、煤等矿产的开采规模扩大,邻近的个旧锡矿在明代后期已初具规模,为滇南矿冶业奠定了基础。滇南地区的纺织、制陶、铁器加工等传统手工业发展,尤其是与马帮贸易相关的马具制造和货物包装业兴盛。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质变:军屯移民带来的租佃制逐渐取代领主经济,货币的流通催生了新兴的市镇经济。至明末,城内已形成“六街九巷”的商业网络,每月朔望之日的集市贸易盛况空前。
明朝进一步扩建元代以来的“步头路”,阿迷州成为昆明至广西、越南驿道的枢纽,设驿站(如阿迷驿)传递公文、维持交通。自元到明清,开远境内有6条驿道,驿道沿途或关隘要地设有2关、3驿馆、4铺舍、14塘、28哨。据史料记载,明中期开远驿站“商贾云集,马店林立”,马帮在此休整、交易。驿道系统加速了边疆与内地的物资、信息流动,便于中央监控边疆动态。本地特产(如矿产、药材、茶叶)通过马帮运往内地和东南亚,形成繁荣的集市经济。
文化熔炉:多元文明融合共生
随着各种军事、贸易、农展等活动,汉族人口逐渐流入,开远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。汉族的大量流入,带来了中原、江南等先进地区的汉文化。地主经济逐渐取代落后的农奴土司经济,生产力进一步发展,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。当时的临安府下辖6州5县,阿迷州就属于6州之一。但与后来的“滇南锁钥”“旱码头”不同,明代的阿迷州地处偏远,发展层次不高。据考证,明朝临安府8个州县中,阿迷属于“简缺”等级,相当于“穷乡僻壤”,在临安府各州县中排名靠后。
明代移民浪潮引发的连锁反应深刻改变了阿迷的文化面貌,造就了开远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高峰。当江南士子携带四书五经踏上这片红土地时,本土精英也展现出惊人的文化适应力。本土进士王廷表与杨升庵两人长达40年的友情,两人纵情诗才写下《双百梅花诗》,是明代阿迷文化繁荣的重大标志。此时,科举制度向边疆延伸,明廷在阿迷州设立州学、社学,鼓励土司子弟入学,学习儒家经典。部分土司后裔通过科考融入士绅阶层,阿迷州彝族上层逐渐接受汉式姓氏、礼制。明代后期,随着汉族移民增加,关帝庙、城隍庙等汉地信仰场所陆续建立,佛教、道教在阿迷民间传播,与本土原始宗教(如彝族的毕摩信仰)共存,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。
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地名系统的重构:原本纯粹的彝语地名开始叠加汉语意象,“马者哨”这类彝汉合璧的名称,恰似两种文明交融的活态化石。明代以前,阿迷只有彝语地名,明代开始,出现了很多彝汉复合的地名。从地域上看,开远坝区多汉名村寨,东山多彝语村落,而西山因是通往临安沿途,又较多汉族村庄。明末清初汉话成为官方话语,形成了一些先汉话后彝语的地名,比如大鲁那、大矣那味等。如今的“乐白道”最初来自彝语“鲁背刀”,明代之前就已存在,清朝时期叫“罗白道”,后演变为“乐白道”。即使是1984年编的《开远地名志》中,全市少数民族地名还有225个,占到全市村寨的49%。

站在21世纪的时空坐标回望,明代阿迷州的蜕变历程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启示。当我们在分司巷触摸斑驳的青砖,不仅感受到土流并治的历史阵痛,更能领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逻辑。这种将边疆治理转化为文明共建的智慧,至今仍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。
 滇公网安备53250202000205号网站标识码:5325020004
滇公网安备53250202000205号网站标识码:5325020004 x
x
 无障碍浏览
无障碍浏览 长者模式
长者模式




 首页
首页

 开远概况
开远概况

 政务资讯
政务资讯

 政府信息公开
政府信息公开

 政务服务
政务服务

 政民互动
政民互动

 投资开远
投资开远